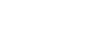文/ 布魯斯.D.培理(芝加哥西北大學芬伯格醫學院兼任教授、兒童創傷事件專家顧問)、瑪亞.薩拉維茲(神經科學記者)
譯/張馨方
走進戒備森嚴的監獄總令人提心吊膽:經過門口仔細的身分檢查後,必須交出身上的鑰匙、皮夾、手機與其他任何可能被偷或被當成武器的物品。除了衣服,任何能表明身分的東西都會被沒收。經過第一道上鎖的大門,上頭的標示寫著「過了這裡,如果你遭到囚犯劫持為人質,獄方概不負責」,這表面上雖是防止訪客假裝遭囚犯劫持以幫助他們逃獄,卻也帶給人不安的感覺。
之後,走過至少三、四扇厚重的鐵門,每扇鐵門都有兩道鎖,門與門之間有重重警力與電子保全防護,每走過一扇門,沉甸甸的柵門就會砰然關上。終於,我見到了要面談的囚犯──利昂,他在十六歲時喪心病狂地謀殺兩名少女後強姦她們的屍體。
從維吉妮亞與蘿拉的案例,我們看到,幼年時期缺乏照顧,會妨礙大腦發展掌管同理心與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區域,這樣的不幸通常會使個案與人互動時感到不自在、覺得孤單與不擅社交。然而,小時候經歷情感剝奪的人,也傾向對人懷有敵意,或是不願意與人來往,幸好,那對母女儘管同理心發展不完全,長大後依然富有道德感;童年時期的經驗使她們不擅於表達情感,而且通常不會注意社交線索,但是卻未滿懷憤怒與憎恨。
利昂的故事則呈現了更危險的潛在結果,幸好,這種案例並不常見。他讓我認識到,父母對孩子的忽視(即使不是刻意的)會造成多少傷害,以及現代西方文化是如何破壞傳統上保護許多孩子不受忽視的大家族網絡。利昂被判死刑,他的辯護律師聘請我在審判的量刑階段出庭作證。
這場聽證會將決定判刑時是否應考量「減刑」因素,例如利昂是否患有心理疾病或曾受過虐待。我的證詞將幫助法庭決定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培理博士將在法庭上,為一名殺人姦屍的少年犯評估他的精神狀況(圖/Pixabay)
***
我在一個暖和宜人的春日來到監獄,那天天氣晴朗,大多數的人看到,應該都會覺得生命無限美好。鳥兒輕快的啁啾聲與溫暖和煦的陽光,與我面前巨大的灰色建築十分不搭調。那是一棟五層樓高的水泥樓房,設有欄柵的窗戶只有幾扇,有面牆的前方建有一間門口漆成紅色的綠色警衛室,與體積雄偉的監獄相比顯得非常不調和。建築外面圍有六公尺長的鐵絲網,上頭還加了三圈刺鐵絲網。
當時只有我一個人在監獄外面。停車場上有幾部老舊的車子。我走向紅色門口,心臟跳得很快,手心也在冒汗,我告訴自己要鎮定。這個地方看起來充滿了肅殺之氣。我走過一扇雙開柵門,通過金屬探測器、接受搜身,然後被一個看起來像囚犯一樣遭到禁錮、滿腹憤恨的警衛帶到監獄裡面。
「你是心理學家?」她懷疑地問我。
「不,我是精神科醫師。」
「隨便,反正你有可能一輩子的時間都會耗在這裡。」她鄙視地笑著說。我勉強擠出笑容。「這是規定,一定要看。」她交給我一張文件,「不可以帶違禁品和武器,不可以帶禮物,也不能從監獄裡帶走任何東西。」我不喜歡她的口氣和態度。她這麼憤世,也許是因為天氣這麼好,她卻得待在監獄,又或許是她覺得與法院合作的心理治療專業人士大多都是來幫助罪犯逃避刑責的。
「好的。」我試著保持禮貌。但是,我看得出她對我已有成見,難怪她這麼有敵意。我們的大腦會適應環境,而這個地方看來很難激發善意或信任。
***
面試室很小,只有一張鐵桌與兩張椅子。地板鋪著冷灰色、有著綠色斑點的磁磚,牆壁由煤渣磚砌成。兩名男警衛把利昂帶進來,他身材矮小,看起來稚氣未脫,身穿橘色囚衣,戴著手銬與腳鐐。以他的年紀而言,他過於瘦小,看起來也沒有危險性。他一臉凶狠,我也注意到他的前臂有囚犯的刺青,是一個彎彎曲曲的「X」,然而,他的凶狠只是虛張聲勢,就像一隻瘦小的公貓為了讓體型膨脹而豎起毛髮。
很難相信,眼前這個剛滿十八歲的少年曾殘忍地殺了兩個人。 他在住處大樓的電梯遇見那兩名少女。雖然當時是下午三、四點,但他已經喝了一些啤酒,他以粗俗的言詞挑逗她們。不出所料地,女孩們拒絕了他,而他尾隨她們進入公寓,經過一陣扭打後用餐刀刺死她們。

▲當時16歲的利昂殺害、並性侵了兩個拒絕他搭訕的年幼少女/示意圖/記者季相儒攝
雀里絲十二歲,她的朋友露西十三歲,兩人幾乎都還沒開始發育。利昂的攻擊來得太快,加上他的體型比她們大,因此兩個女孩沒能自衛。利昂很快地用皮帶把雀里絲綁起來,之後,露西試著反抗,於是他殺了她,可能是為了不留下目擊者,或是還在氣頭上,他又殺了雀里絲。接著,他強暴了兩人的屍體,怒氣未消的他還對屍體又踩又踹。
雖然他經常因為惹事生非而被警察抓,但從過去的記錄看來,他並不像是會犯下這種大罪的人。他的父母是努力工作的合法移民,沒有任何犯罪記錄。他的家庭從來沒有涉及兒童保護服務,沒有家庭暴力、寄養安置或任何依附問題的癥兆。然而,他的記錄顯示,他十分擅長操弄身邊的人,更不妙的是,他沒有任何親近的人。別人常形容他沒有同理心:不知悔改、冷酷無情,不怕校規,也不受少年感化教育的影響。
我看到他年紀輕輕就被關在這座可怕的監獄,為他感到難過。之後,我們開始談話。
「你就是他們安排的醫生嗎?」他失望地問。
「是啊。」
「我有說我想要女的心理醫生耶。」他輕蔑地笑著說。他把椅子推開,踹了幾腳。我問他是否有和律師討論過我要來探訪的事情以及面談的目的。
他點點頭,試著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但我知道他一定嚇壞了。他或許不會承認或甚至意識到這件事,但他確實隨時都處在警戒狀態,時時刻刻都在觀察周遭的人,看誰能夠幫他、誰會害他,找出別人的弱點,弄清楚別人要什麼、害怕什麼。
我從走進面談室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他也在觀察我,試圖找出我的弱點、摸索操弄我的方法。他很聰明,知道典型的精神科醫師心胸開闊、過度善良;他已經成功掌握檢察官的心理,讓她開始同情他,甚至還說服她,他是冤枉的。

▲利昂謊稱他和兩名少女是合意性交,只是發生了點誤會/示意圖/記者徐文彬攝
他讓檢察官相信,是那兩個女孩邀他到家裡,而且承諾要與他發生性關係,後來事情變調才發生意外。他不小心絆到她們的屍體,所以靴子上才有血跡。他從來都沒想過要傷害她們。而現在,他也想說服我,那兩個少女是挑逗與勾引他的賤貨,他才是受害者。
「跟我說說你的事。」我先提出開放性的問題,想聽聽他會怎麼說。
「什麼意思?這是精神科醫師的把戲嗎?」他猜疑地問。
「沒有,我只是想,你最能告訴我你是怎樣的人。我聽了很多人對你的看法,老師、治療師、觀護人和記者等等,他們都說了自己的意見。所以我也想聽聽你的說法。」
「你想知道什麼?」
「你想告訴我什麼?」我們就這樣一來一往地繞圈子。這個伎倆我再熟悉不過了,他很厲害,但我也經驗豐富。
「好吧,那說說現在,在監獄裡的生活如何?」
「很無聊啊。感覺還好,沒那麼糟,但沒什麼事可做。」
「說說你一天都在做什麼。」
他開始敘述,說到監獄裡的作息與之前在少年監獄的經驗時,感覺慢慢失去戒心。我讓他盡情地說,過了幾個小時,我們休息一下,讓他抽根菸。我回來時,決定切入重點。
「跟我說說那兩個女孩發生什麼事。」
「真的沒什麼啊。我只是到處晃晃,然後遇到她們。我們聊了一下,她們問我要不要去她們家玩。到家後,她們又改變心意了。我很不爽。」這跟他最初和後來的說詞都不一樣。看來距離犯罪的時間點愈來愈遠,他把事情描述得愈來愈不凶殘。每次他敘述事發經過,都慢慢推卸責任,讓自己逐漸取代那兩個女孩,成為受害者。
「那是意外。我只是想嚇她們,但那兩個愚蠢的賤貨就是不閉嘴。」他繼續說。我的胃在翻騰,但我告訴自己,不要有任何反應,保持冷靜,如果他察覺我的恐懼和作噁,就不會說實話。要冷靜。我向他點點頭。
「她們有大叫嗎?」我努力不帶情緒地問。
「對啊。我跟她們說,如果她們閉嘴,我就不會傷害她們。」他對我描述一個簡短、經過粉飾的版本,沒有提到強姦,也略過他是如何殘忍地踐踏女孩們的屍體。

▲利昂在殺死兩名少女後還不罷休,侵犯並毀壞她們的屍體/示意圖/記者周宸亘攝
我問他,女孩們的尖叫聲是否激怒了他,所以他才會踢她們的屍體。解剖報告顯示,那名十三歲女孩的臉部、頸部與胸部都有遭到踩踏的痕跡。
「我沒有踢她們,我是被屍體絆倒。你也知道,我喝了一點酒。」他的故事裡留了一些空白,希望我會自己填補完整。他看我的表情,想判斷我是否相信他的謊言。他的表情或聲音沒有什麼情緒,描述謀殺經過時,就像在課堂上做報告一樣;他顯露的唯一情緒是不屑,對我表示,是那兩個女孩讓他不得不痛下毒手,她們一直反抗,讓他很生氣。
這個男孩的冷血令人震驚。他是個掠食者,只在乎能夠從別人身上得到什麼、能夠驅使別人做什麼,以及如何利用別人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在辯護律師請來的心理醫生面前,他甚至無法裝出有一絲同情心的模樣,枉費律師還期盼能從他身上找到最後一點良心或希望。
他並不是不知道應該試著裝出悔恨的樣子,但他只會利用別人,無法顧慮別人的感受。他沒有同理心,因此也無法偽裝得很好。利昂並不笨,其實,他的智商在某些方面遠超過平均值,但是整體成績參差不齊。雖然他的語言智商低於正常範圍,但他的操作分數(包含推理與空間能力等)卻是相當高。他在解讀社會情境與理解他人意圖的方面,分數特別出眾。
這種語言與操作表現的差異,經常可見於受虐或創傷兒童的身上,這也凸顯了他們大腦某些區域的發展需求並未獲得滿足,尤其是位於下層、比較敏感的皮質區。一般人口中,約有五%的人呈現這樣的模式,但在監獄與少年感化院中,比例超過三十五%。這種現象反映了大腦的使用依賴性:
在成長過程中面對愈多混亂與威脅,大腦的壓力反應系統與負責解讀與威脅相關的社交線索的區域發展得愈多;小時候缺乏關愛與呵護,就會導致掌管同情心與自我控制的系統發育不良。智商測試結果是第一個線索,指出利昂的童年可能出了問題。
我試圖從面談中了解他在幼年時期發生了什麼事,但進展不多。畢竟,多數人不太會記得出生後到上幼稚園這段關鍵發育期當中發生了哪些事。然而,有證據指出,他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出現問題,記錄顯示,他在幼稚園時期已有攻擊行為。從我們的談話也可以感覺得出來,他沒有幾個朋友,除了家人以外也沒與任何人建立長久的關係。
他曾經霸凌別人,也犯過偷竊等小罪,但直到這次才被關進成人監獄。他在青少年時期的罪行大多獲得緩刑;儘管犯下一些嚴重的傷害罪,卻沒有在少年觀護所待多久。
雖然如此,我發現他犯下、或疑似犯了數起傷害罪,但由於證據不足,因此沒有遭到起訴或定罪。例如,他有一輛腳踏車被人發現是贓物,而身為車主的青少年被打成重傷,因為有生命危險而被送醫急救。不過,這次的攻擊沒有目擊者(或是沒有人願意挺身作證),因此利昂只被以持有贓物罪起訴。之後,我到監獄與他面談了幾次,他開始吹噓自己的性侵經驗,態度與先前描述謀殺案的時候一樣冷酷輕蔑。
我想知道他有沒有一絲悔恨,最後問了他一個本來應該是很簡單的問題。
「現在回頭想想,如果再重來一次,你會怎麼做?」我期待他至少能吐出一些陳腔濫調,說自己會控制脾氣、不會傷人之類的話。
他想了一下,回答:「不知道,可能把靴子丟了吧。」
「丟掉靴子?」
「對啊,就是靴子的鞋印和上面的血跡害我被抓的。」
***
換做是其他精神科醫師,一定會有很多人就這麼離開監獄,認為利昂是個「壞胚子」,天生就是個怪胎、沒有同情心的惡魔。儘管基因傾向似乎會影響大腦牽涉同理心的系統,但我根據自己的研究認為,像利昂如此極端的行為,大多都出現在幼年時曾遭遇某種情感與/或生理剝奪的人身上。
此外,如果利昂具有增加反社會行為風險的基因(假使這種基因真的存在的話),那麼他的家人或親戚──如父母、祖父母、甚至叔叔等──應該也會有類似或比較輕微的前科才對,譬如曾遭到多次逮捕。另外,利昂是因親哥哥報警而被抓的,他的哥哥看起來與他截然不同。
利昂的哥哥法蘭克*與父母及其他親戚一樣,收入穩定。他是個事業有成的水電工,已婚並育有兩個小孩,在社區裡受人敬重。利昂犯罪那天,他回到家,看到利昂坐在客廳看電視,腳上還穿著染有血跡的靴子。電視上的新聞快報說利昂住的大樓有兩名少女慘遭殺害。法蘭克不經意瞥到利昂腳上的靴子,等到他離開,便打電話報警,表示自己的弟弟涉嫌犯案。

作者: 布魯斯.D.培理、瑪亞.薩拉維茲
本文由 柿子文化 授權轉載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