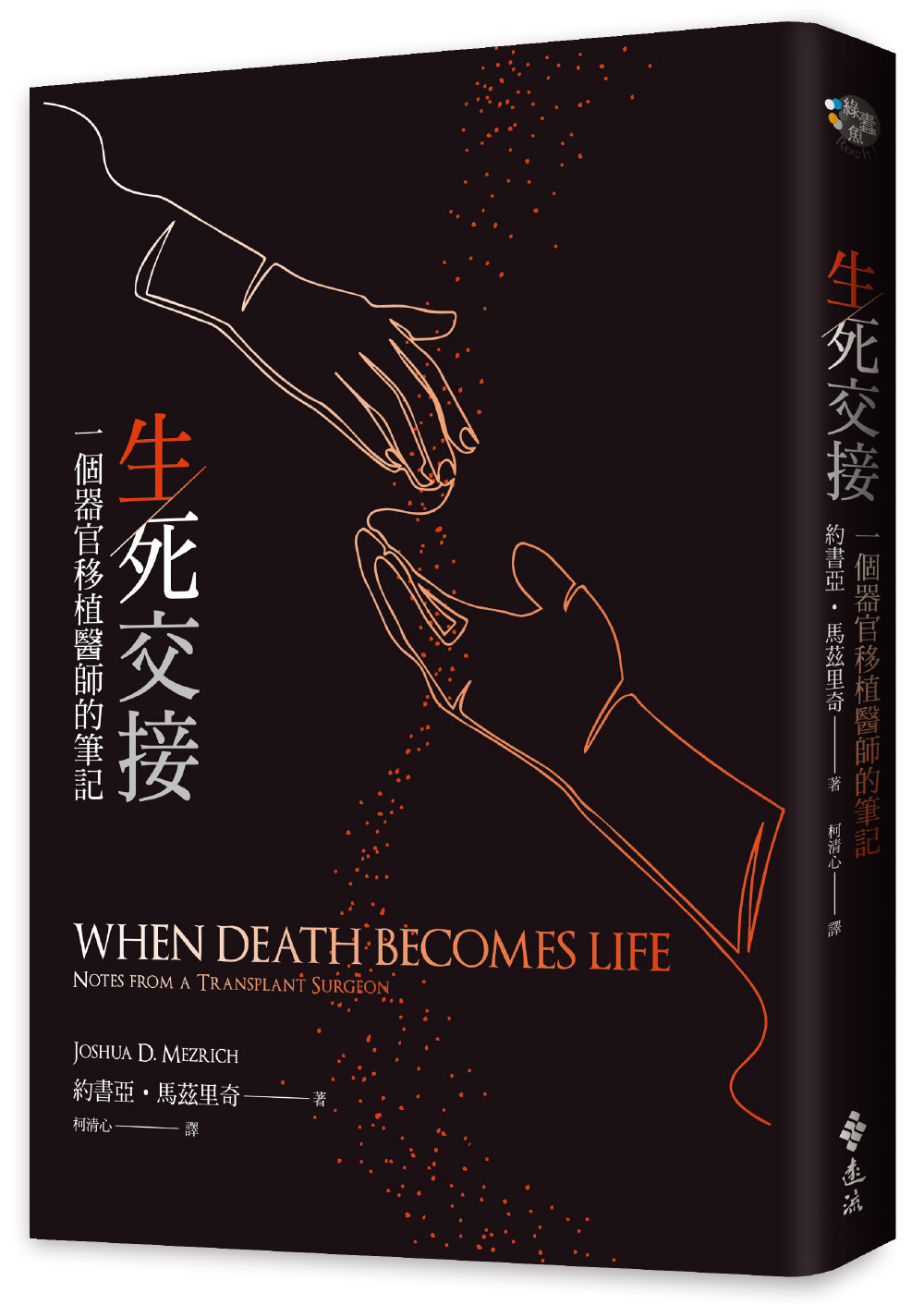文/約書亞‧馬茲里奇(器官移植醫師)
譯/柯清心
「你們有多少人認為,我們應該幫酒鬼做肝臟移植?」
約莫半數的人慢慢舉起手,其他學生則不安的四下環視。這些是醫科三年級的學生,我正在做每個月的器官移植演說。
「有多少人覺得,潛在的受贈者在做移植前,應該有六個月不沾酒?」
這回很多人都舉手了,且大部分學生臉上都透著自信。如果患者想做難能可貴的肝臟移植,就應該保持清醒,這可是最終的保命資源啊。
「可是如果他們活不過六個月呢?假如他們接下來兩週就會死掉呢?如果患者是位有三個孩子的三十七歲母親,或二十六歲的大學畢業生,根本不懂他在糟蹋自己的肝臟?你們會忽略那幾個幼兒的存在,而放任他們的母親去死嗎?你們會站在年輕人前面,在他父母的注視下,告訴他說,你可以救他,可是你認為他不配嗎?」
我接著問:「你們有多少人認為酗酒是一種病?」
幾乎每個人都舉手了。
「你們認為,在肝移植後,這種疾病的復發率是多少?」
少數幾個人猜20%,約略是正確的。
「有多少人認為C型肝炎是一種疾病?」
每個人都認為是。
「移植後的復發率呢?」
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該為C肝患者做移植嗎?同樣的情形,不也能用在NASH上?」我問他們,NASH指的是因肥胖、糖尿病和高膽固醇等非酒精因素所造成的脂肪肝。
「我們不該為肥胖的人做移植嗎?那些因糖尿病控制不良或高血壓而造成的腎衰竭患者呢?」
早期做肝臟移植時,一般認為拯救酒精性肝病患者是在浪費有限的資源,但現在已經轉向,改為支持這種治療了,因為資料顯示,這些移植的結果跟其他病況的結果一樣或者更好,所以政策變了。
許多醫療計畫要求候選者至少要六個月不能碰酒。為什麼?夠資格的患者,在移植後就比較不可能回去喝酒了嗎?萬一某個患者肝臟病重到根本無法喝了呢?等待那六個月,可有任何人受益?
全美許多移植中心都採行六個月的規定,這項規定來自一項回溯性研究:追蹤四十三名因酒精性肝病而做移植的患者。
在這份分析中,移植前戒酒少於六個月被視為復發的危險因子。許多進一步的研究對於到底要戒酒多久才能滅低術後復發或重新酗酒的情況,答案則十分模棱兩可。
更令人混淆的是,法國(在法國基本上得喝酒)最近有份研究顯示,經過精挑細選,患有嚴重急性酒精肝炎的病人肝臟移植的成效一樣好,而且跟那些戒酒六個月才移植的患者復發率相似。
我曾經為一些喝完酒後幾天因急性肝臟衰竭入院的病人開過非常成功的刀,也曾為一些好幾年滴酒不沾的患者做過極其失敗的手術。
記得有個二十七歲的患者,有嚴重焦慮失調症和急性酒精性肝炎,他只差幾天,甚至幾小時就要去見閻王了。這位患者做完移植後,人生徹底翻轉(他的復原過程極其辛苦),而且還返校讀書。
記得有個偷喝酒的年輕母親,又重新投入她的家庭和職業。我還深刻記得,一位有三個孩子,聰明、成功、討人喜愛的父親,在住院時那種羞愧懊悔的表情;因為他故態復萌,戒不掉這要人命的東西,導致移植的肝臟舊病復發。
我一直在苦惱這個問題--我們到底該不該為酒鬼做移植?誰才是接受這份生命之禮的正確人選?到頭來,我還是沒有答案,但也許我的病人有。

▲該不該為酒鬼進行肝臟移植手術,讓醫師苦惱不已。(示意圖/CFP)
★ 版權聲明:圖片為版權照片,由CFP視覺中國供《ETtoday新聞雲》專用,任何網站、報刊、電視台未經CFP許可,不得部分或全部轉載,違者必究!
莉莎的故事
我仍記得第一次見到莉莎的情形,我剛巡完診,決定到她病房一下,跟她談談我對肝臟移植的看法。我只知道她還年輕,四十一歲,而且生病了。她的MELD指數三十二,病症是酗酒。
我走進莉莎的病房時,被她的某種特質嚇了一跳。她有著清新年輕的容貌,美麗的笑容,她雖然病黃腫脹,卻透著愉悅,而且在重病患者的恐懼與焦慮下尚可見到一絲的調皮。莉莎的眼神散出淡淡哀愁,她了解自己做了什麼,才會來到這裡。這跟我聽到有個已經戒酒一年多、酒精性肝硬化的女患者時所想像的不一樣。
我回到辦公室後,在做筆記前先翻閱她的病歷,特別仔細看她的AODA評估(酒精與其他藥物濫用),那是我們規程的一部分。這份評估跟我們第一次會面時,我火速翻閱她的病歷時是相符的。莉莎喝紅酒──通常一天不超過兩杯。她年輕時喝得更多,但現在不會了。她以前藉酒抒解焦慮,焦慮源自她年少時受到的攻擊,但她發現自己生病後,就不再碰酒了。
我讀著報告,一開始以為酒精在她的肝疾中也許占了一部分角色,但或許不是主因。我們從來無法知道一個人要喝多少酒才會造成肝硬化。一般而言,我們認為男人每天喝超過兩杯,女人超過一杯,便可能喝多了,但是大部分喝到這種程度的人,並不會造成肝病。許多其他因素也會造成肝硬化,從遺傳因子、肥胖(造成脂肪肝),到單純的運氣差都有可能。
我們還知道,人們若被醫療專業人員問起,往往會少報自己喝的酒量,因此,我們通常會照例把患者所說的數量加倍──尤其考慮幫他們換肝臟時。儘管如此,我認為莉莎復發的風險很低,也許是因為我一眼就喜歡上她吧。連我這個挺享受喝酒的移植大夫也很想相信她真的沒有喝那麼多。
莉莎的肝臟移植術非常直截了當,我們在她腹中發現五公升左右的啤酒色腹水,以及一副扁縮硬化的肝臟,我們把它從沾滿血的黏著物中切出來,一直維持在正確的組織平面裡,從未失控,我們無須把音樂轉低,或停下我滔滔不絕的笑話。
我們把新肝臟帶到手術區,讚嘆它的美麗。我們接上所有的血管,然後鬆開鉗子,望著肝臟變成粉紅色,恢復生機。不久之後,肝臟便開始從膽管流出漂亮的黃色膽汁了,我們知道不會有問題了。我們縫接管道,把捐贈者的器官縫到受贈者身上,最後再四處檢視有無流血之處,然後為莉莎縫合。
手術非常順利,莉莎還在手術台上,我們便拔除她的呼吸管了。我們得意的將她推到恢復室,然後我下樓去跟她家人說話。一切都很好,時間下午四點,我甚至可以來得及回家吃晚飯。很棒的一天。
莉莎的康復過程很平順,她出院三週後來看我的門診,身上的黃疸已經消失了,多餘的液體已從體中排除。她看起來就像一位我口中的「老百姓」,不再是穿著醫院病袍和拖鞋的標準病人。她的笑容依舊,哀愁的眼神似已消失無蹤。我會很快的把她轉給我肝臟科的同伴,艾列克.穆沙特醫師了(Alex Musat)。
兩個月後,艾列克看到莉莎時,她的肝指數完美得不得了,她對自己的恢復也很滿意,再度享受自己的家庭與生活。艾列克安排她六個月後回診--但莉莎並沒有出現。然後,在她移植後的十個月,莉莎因為嚴重肝功能失調又住院了,她的皮膚跟剛開始時一樣黃,肝臟切片顯示她又酗酒了。
我去看她,她又泛出淡淡的黃疸,穿回標準的病袍。我尷尬的旁敲側擊,探問酗酒的問題,最後終於問她在移植後是否又開始喝酒了。她跟我保證說她沒有喝,她上次沒回來做追蹤,還有過去幾個月沒做檢查,是因為她很忙--她這麼對我說。我表示她若再酗酒,這副新的肝臟很快便會衰竭。
當然了,我們沒有人相信她的話。不幸的是,這種情形我們以前也見過。接下來幾年,莉莎因肝功能嚴重失調而進出醫院。有一陣子,她一直否認自己喝酒,最後才終於承認只喝了一點點。
她移植不到五年,我便收到她去世的電郵通知了。我知道她的肝臟掛了,而事情不可能以別的方式結束。然而,她的死一直在我心中盤踞不去。
我仍能看見她的笑容,依然記得她年輕的家庭和孩子們。這件事為什麼不能出現不同的局面?我們到底錯失了什麼?我安慰自己說,至少她的家人多享受了幾年陪她的時間,就某方面來說,那份生命的賜禮,還是值得的,不是嗎?
作者: 約書亞‧馬茲里奇
譯者: 柯清心
本文由 遠流出版 授權轉載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