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志宏案中,警方未隨案移送其行蹤交代稿,成為新證據而開啟再審。依據冤錯案經驗顯示,往往與案件初期警察的偵查瑕疵有關。(圖/記者林悅翻攝)
謝志宏在2000年被指控與郭姓共同被告共同殺害兩名被害人,判決死刑定讞,2018年台南高分檢檢察官為謝志宏提起再審,日前台南高分院裁定開啟再審並停止執行,謝志宏當庭獲釋。法院開啟再審是基於三項新證據,分別為謝志宏所撰寫之「行蹤交代稿」、鑑定人出具之「犯罪現場重建鑑定報告」,以及刀具「血溝」設計之疑點。
做為法律學者,這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行蹤交代稿」。
依照台南高分院新聞稿所述,所謂的行蹤交代稿是謝志宏當年在警詢自白前所寫,內容否認所有犯罪,並表示所有犯行均為郭姓共同被告所為,與謝志宏後續之辯解均大致相符。這份行蹤交代稿之所以會成為新證據,是因為這份重要的證據停留在警察的檔案裡,當時並未附卷隨案移送,所以原審法院並未審酌過此項證據。經過再審法院調查,謝志宏寫完這份行蹤交代稿三、四小時後,就在警詢時承認殺害兩名被害人,同時亦承認不實之性侵害犯罪,過程中沒有錄音、錄影,這樣的轉折讓裁定開啟再審之法院,對於謝志宏自白的可信度感到疑惑。
我國的訴訟體制是採取「卷證併送制」,也就是理論上所有案件的卷證都會透過檢察官移送至法院,再由法院透過閱卷制度讓被告及辯護人知悉卷證內容,擬定防禦策略。理論上這是一個自動的資訊交換過程,最終可以讓被告及辯護人知悉「所有」有利及不利被告之證據。相對的,美國是採取「證據開示制度」,被告及辯護人資訊的獲取是透過與檢察官之間的談判與開示,被告最終很有可能無法取得全面的卷證資料。就被告的權利而言,我國現行的閱卷制度明顯優於證據開示制度,因為重要證據通常是自動轉交給法院,不太可能會「卡關」。
但是謝志宏案告訴我們,這個資訊移交過程仍存在漏洞,原來重要證據有可能停留在警察手中,如果檢察官也沒有拿到完整的資訊,後續審判制度無論如何完善,都是徒勞無功。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在冤案中發現資訊不流通的問題。
在另一件張月英案中,也是在提起再審的過程中,才發現原來警察手中握有案發前一小時張月英在非案發地點撥打電話的通聯紀錄,警察當時認為這項證據不重要,因為在一小時內張月英有可能從撥打電話的位置移動到案發現場,因此警察選擇不將這份資訊附卷呈交給檢察官及法院。但是對張月英來講,這項證據卻是重要的不在場證明,因為可以與她的證詞及其他證人的證詞相互佐證,證明她當天案發時,人不在案發現場。
我們必須思考,一項證據是否重要?要不要附卷讓檢察官、法官、被告及辯護人知悉?這件事應不應該交給警察做決定?警察作為第一線的犯罪偵查者,勢必是以偵查者思維看待證據,更會受到各種時間壓力、社會輿論及組織文化而影響其客觀性。這不是警察的錯,而是制度上就是如此設計。因此,制度設計上應該是要求警察「無差別」地將蒐集到的證據放入卷中,再讓後續的審、檢、辯三方透過程序機制,決定應該如何評價或是詮釋這些證據。在英國,甚至設有專法要求及確保警察將所有可能有利被告之資訊都附卷,讓檢察官能做更進一步的判斷。
警察作為司法的第一線,但是在司法改革的討論中卻常常消失無蹤,社會或許應對警察的改革投入更多的關注與資源,因為冤錯案的經驗顯示,冤錯案往往與案件初期警察的偵查瑕疵有關,且這樣的瑕疵在後續程序中,往往無法透過司法程序機制而獲得填補。
好文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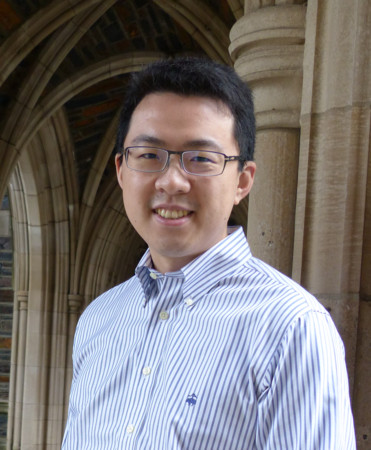 ●金孟華,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金孟華,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