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發生的后豐大橋女老師墜橋案,男友王淇政(左2)與友人洪世緯(右2)於2019年底再審宣判無罪 。(圖/記者白珈陽攝)
2002年12月7日,陳姓女子自台中后豐大橋墜橋身亡,案件在台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為罪嫌不足,在2004年9月對王淇政和洪世緯二人做出不起訴處分。本來應該到此為止的案件,因為在2005年1月間有證人做出了不同於過往的證述,檢察官轉而起訴王淇政和洪世緯,也開啟兩人後來長達十年的冤獄人生。
案件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轉折,正是因為在事發兩年後,有證人變更了他原來的說法,轉而做出不利於王淇政和洪世緯的供述。至於證人說法以外的事證則沒有任何的變化,一樣沒有其他可以認定兩人犯案的證據存在。也就是說,本來被認為是罪嫌不足的案件,因為一個證人更改了他本來的證詞,就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由此恰恰可以看出證人供述在法官或檢察官心中的重量。
但是,證人的供述如果沒有其他的具體事證支持,其實是一種非常不可靠的證據類型。證人的供述會因為動機或目的而有所差異,先不談惡意說謊,如果證人主觀上認為或懷疑法庭上的被告是實際的犯罪者,他的證述難免往不利於被告的方向進行,或者是提供被告可能是實際犯罪者的想像給法官或檢察官。
除了證人主觀上的動機或目的外,證人說詞是否可信,也會因為證人的知覺、記憶及陳述能力而有所影響。
所謂的知覺,就是證人就其見聞的感受,因為每個人對於外界的感受和觀察能力不同,因此,即便是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人可能就會有不同的觀察結果。舉例來說,同樣的一台汽車,有的人可能會認為是白色,有的人可能會認為是銀色,但是車色可能就會影響事實認定的關鍵因素。
關於記憶的部分就比較容易理解了。通常做證的時間點都會距離事發後一定的時間,時間就會考驗人的記憶能力,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長時間記得事發時所見聞到的所有事實,但是,無論是審判程序或是偵查程序,期望每個人都能夠記得每一件事,以至於證人必須在司法程序中,就其無法記憶的事項做證,法官或檢察官甚至可能將這些證人因為無法記憶所推測、隨意回答,或迎合詢問者所提出來的證述,做為認定被告是否有罪的依據。
陳述能力則是指每個人能否順利、完整的將心中想法表達出來,讓其他人可以確實接收並了解其內容。每個人的人生經驗、學經歷背景和臨場反應都不相同,基於這些不同,每個人在說話時所使用的詞彙、講話的邏輯和結構、表達的方式與程度,對外界所產生的效果都會不同。有些人自認為講的很清楚,但聽的人未必能夠真的理解;有時候講的人講的不明不白,但聽的人卻自以為聽的很明白。
正因為人的供述有上面談到的不確定性,因此,單憑證人的說法就做出判斷,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也是難以確認真相的。也因為如此,人的供述不應該在事實的判斷上承載過多的重量,也就是說,人的供述應該只是輔助的性質,只有在其他客觀事證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夠用以輔助認定事實,而不是反過來以人的供述做為認定事實的核心。
后豐大橋案所彰顯的正是司法實務上,以證人供述為核心的判斷結構;證人前後不一的說法,導致法官和檢察官對於王淇政和洪世緯兩人有沒有犯罪,做出截然不同的認定,殊不知,案件中存在著多項與證人證詞相左的客觀證據。過去的判決就因為執著於證人的供述,而忽略了其他客觀上都足以推翻該名證人證述的證據。
以人的供述做為認定事實核心的審理方式,往往賦與人的供述過多的證據價值。由於人的供述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因素,無法、也不應該單獨做為認定事實的依據,人的供述應該只能用以輔佐其他客觀證據,沒有客觀證據支持的供述,在法庭上不應該是有任何的價值或份量。只著重證人供述的結果,往往就是產出冤錯案件的關鍵。
好文推薦
 ●林俊宏,義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及司法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刑辯工作坊交互詰問課程講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官網http://twcdaa.org。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林俊宏,義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及司法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刑辯工作坊交互詰問課程講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官網http://twcdaa.org。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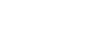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