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建和案在刑事法庭折騰近二十年,終於判決無罪,但平冤了卻非終點,如今還面臨著可能要賠償受害者家屬。(圖/記者陳豐德翻攝)
1991年8月,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無辜捲入汐止吳氏夫婦命案,遭警察嚴刑逼供後,於1995年被判處死刑定讞,羈押在看守所中面臨隨時被槍決的恐懼及痛苦。筆者身為辯護律師挺身聯合幾位同道義助替蘇案三人尋求平反,超過四分之一世紀,年屆耄耋之年,整個磨難過程令人刻骨銘心。
所幸在2012年8月31日,經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庭(100年矚再更三字第1號)作出無罪判決,因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8條規定,自本案第一審繫屬開始已超過六年,且最高法院發回三次以上,連同更三審無罪判決在內,高院已有三次無罪判決,檢察官不能再濫行上訴,全案終於無罪定讞,結束21年生死纏訟的漫長日子。
無罪平反後,隔年國家也依《刑事補償法》規定,裁定蘇建和、劉秉郎各獲542萬1,000元,莊林勳獲500萬4,000元補償金,聊表認賠贖罪之意。
當社會大眾都以為這件耗時多年的冤案已經落幕,然而,被害人家屬早在1992年檢察官起訴後,對蘇建和等三人提出了刑事附帶民事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訴訟。為求妥速,刑事第一審有罪判決後,即將民事求償部分裁定移由士林地方法院分開審理。經民事庭第一、二審皆判決被告三人免賠,其主要理由在於當年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作成的鑑定報告,推認被害人係遭3種以上刀器所致,但扣案菜刀具有5個角3個切面,可能導致被害人身上的各種傷勢,無法以兇刀認定犯案者除了王文孝外,另有他人。
特別是此種論斷,在刑事訴訟程序再審時,法院曾委託國際刑事鑑識權威李昌鈺博士進行鑑定,依鑑定結論確認被害人共受79處刀傷,但並非砍殺79次,也許一刀多傷,而現場發現3枚血指紋都是王文孝的,並無蘇建和等三人的指紋及毛髮等微物跡證存在,因此認定極可能為王文孝一人所為。法院認為,李昌鈺博士的鑑識專業能力為國際肯定,該鑑定報告依現存資料進行現場重建,以其專業認為極可能為王文孝一人所為的結論可採信,因此僅判決真兇王文孝一人需賠償,但因王文孝已執行死刑,改由其母親(繼承人)負賠償責任。
但被害人家屬不服上訴三審後,最高法院竟於2020年8月26日將本案民事判決部分廢棄發回高院更審,這意味著自案發至今已逾31年,蘇建和等三人仍要在司法另一場民事審判中繼續遭受煎熬磨難。
今(2022)年5月31日中研院黃丞儀教授在Twitter公開質疑:「如果國家發動偵查權偵辦,當初關押這麼久了,都無法確認他們是不是兇手,民事程序可以查清楚?」令人錯愕的是,最高法院民事庭將本案廢棄發回高等法院的理由中,竟要求蘇建和三人就被刑求逼供事實為舉證。
判決提及:「按刑事訴訟因將剝奪被告之身體自由、財產甚或生命,乃採取嚴格之舉證標準及證據法則,其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而民事訴訟係在解決私權糾紛,就證據之證明力係採相當與可能性為判斷標準,亦即負舉證責任之人,就其利己事實之主張,已為相當之證明,具有可能性之優勢,即非不可採信。又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民事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參見最高法院108度台上字第1437號判決)
簡單來說,最高法院認為蘇建和等三人在刑事訴訟上因檢察官舉證及被告自白欠缺證據能力的問題,遭法院依無罪推定原則獲判無罪確定,但民事訴訟有別於刑事訴訟,被害人家屬提出刑事案件所為之自白、法醫研究所鑑定報告等證據,在具有可能性之優勢下,蘇建和等人若抗辯遭到刑求,必須舉出反證,證明沒有殺人的侵權行為。此種苛刻的要求,有如登天之難。被告三人遭警方違法逮捕後,所有證據都由檢警採證,當時處於威逼密室無助情形下,並無律師在場見證,又不可能攜帶蒐證器材,試問無辜被告要如何提出反證自己是被刑求逼供?

▲刑事庭已認定「殺人罪不成立」,民事庭卻要推翻刑事無罪判決,要被告為殺人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成司法正義的錯亂。(圖/視覺中國CFP)
最高法院上開說法可能混淆當事人舉證責任,我國《民事訴訟法》學者沈冠伶教授於〈刑事判決對民事訴訟之影響—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評析〉文章中曾闡述:「所謂證明度,係指民事訴訟上某事實被認定(確信)存在所應達到之程度,此係客觀上標準,雖無庸達到如自然科學上證明存在之絕對百分百確信程度或刑事訴訟之不容懷疑(無合理懷疑)程度,但民事訴訟上事實被認定存在之真實程度,原則上仍應具有社會生活上通常理性之人所能相信高度可能存在之程度,俗諺有云,八九不離十,法官之確信應到達此高度之蓋然性。此雖難能以具體數字予以測量為百分之九十或八十,但非以證據優勢為已足。」同篇文章也強調:「對於『被告為侵害行為人』一事,應審慎認定,不宜採取優勢證明或降低證明度。如降低證明度,則較容易認定行為人而使其負侵權行為責任,此與行為責任歸屬法理有所背離,亦可能增多錯誤或寬鬆認定行為人而增加濫訴之風險。」(參見《台灣法學》第405期,第47至64頁)
由此可見,即便是民事訴訟程序,對於證明度的要求,也不因此降低至所謂超過一半即謂已足,否則,無辜者可能因法院採優勢證明遭判敗訴以致須負損害賠償。以本案為例,刑事庭已認定「殺人罪不成立」,民事庭卻要推翻刑事無罪判決,要被告為殺人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僅對冤案當事人形成二度傷害,造成司法正義的錯亂,更重創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況且,與本件民事訴訟基礎事實同一的刑事確定判決中已認定出於刑求的被告自白欠缺證據能力,不得做為證據使用。豈料多年後,該等自白竟「敗部復活」在民事庭中使用,顯然違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禁止酷刑公約》第 15 條所要求:「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以酷刑取得之供詞為證據」之規定,若民事庭法官承認國家違法取得的自白具有證據能力,造成刑事、民事對證據排除法則適用上的衝突,未來恐怕只能交由憲法法庭作出統一解釋,以解決無辜被告的司法磨難。
此外,最高法院於發回意旨中也指出:「系爭鑑定報告(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報告)亦經中央警察大學認具體合理,應得推翻重建鑑定報告(指李昌鈺博士現場重建鑑定報告)」,可知最高法院認為由政府機關作成的鑑定客觀具有權威,優於私人鑑定,這恐怕又陷入另一種迷思。在先進的民主國家,私人的鑑定單位比比皆是,甚至鑑定的權威性還勝過公家鑑定單位。
事實上,本件法醫研究所使用的「刀痕角度比對法」,乃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獨創見解」,沒有任何相類似的科學研究及期刊文獻發表,鑑定人員在欠缺凶器比對的情況下,以超音波與電腦斷層掃瞄儀器,採取死者骨骸上有0度、20度、40度的刀痕角度,就推論至少有三種不同類別的刀刃凶器,兇手不只一人,違背一般「工具痕跡」鑑識的基本常識,十分荒謬。
何況本件法醫研究所的「烏龍鑑定」,主鑑定人蕭姓法醫為另尋求專業機構認同背書,事後於2011年將上開鑑定的豬骨實驗結果發表在國外期刊,題目為:「A Method for Studying Knife Tool Marks on Bone(中譯為:關於骨骸工具痕跡研究)」,且向法務部申請科技計畫經費補助,該法醫於研究結論中已自承:「由於活體骨頭具有彈性,因此在實際研判時,骨頭上的刀痕通常無法反映出刀刃的角度」,顯見前開自創的鑑定方法有錯,違反科學專業及經驗。而中警大也承認僅作形式審查,其背書之正確性亦失去依據。
不論是法醫研究所鑑定報告或中央警察大學審查報告均不被刑案終審法院所採,高等法院100年矚再更(三)字第1號刑事判決特別提到:「法醫研究所骨骸刀痕鑑定部分,有數據錯誤、測量誤差等瑕疵,且不符科學證據的審查標準,中央警察大學審查報告疏未注意及此,是其此部分之報告,自不可採。」最高法院民事庭的法官未能仔細閱卷參按,猶以之為理由草率發回,甚至貶低李博士的科學鑑定,無非想張揚自己的能耐,豈能無愧於心?
眾所周知,國內負責鑑定的單位與追訴犯罪的機關大都是屬於司法系統,球員兼裁判的立場不僅公正性受到質疑,聽從指揮辦案更有先入為主的風險,錯誤、不科學的鑑定比刑求更加可怕,回顧江國慶案、蘇建和案等冤案形成的共通點,除了被告曾遭刑求逼供外,在刑事鑑定上也都曾出現錯誤,以致於造成法院誤判。
國內知名律師陳長文曾以「司法為民,民事也要妥速審判」為題投書媒體(參見2014年7月28日《中國時報》),筆者閱後感觸甚深。良以不論民事、刑事或行政案件,國家都有義務提供「妥速」的司法救濟程序,否則如同本案民事訴訟審理延宕一拖31年,令當事人苦不堪言,國家浪費龐大司法資源,若非新生代再有一群正義律師團自告奮勇義務相護,司法又將如何真正保障人民訴訟權及伸張公理正義呢?
好文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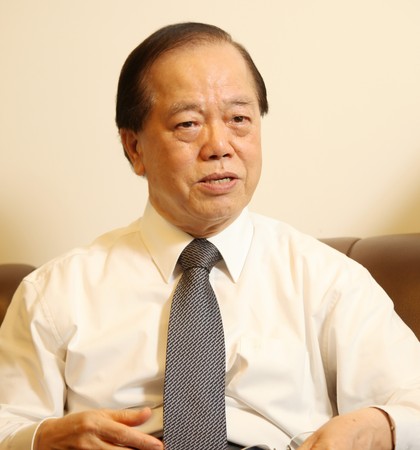 ●蘇友辰,執業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著有《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蘇友辰,執業律師、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著有《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