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明謹/專業足球球評,曾發行雜誌刊物《足球主義》
高雅的徽章
歐洲許多王國,都會使用動物做為標記,以顯示國力的強大,例如英格蘭使用的獅子,或是德國的聯邦之鷹,無一不是用來彰顯自身的威猛,法國是少數使用花朵做為徽章的國家,早在12世紀,鳶尾花就成為王室旗幟、盔甲、硬幣等物品上的重要紋章,鳶尾花象徵著光明和自由,在法國大革命初期,一度因為要推翻君權,鳶尾花被認為是一個需要被摧毀的圖騰,在王室復辟之後,鳶尾花再度成為法國國花。
之後雖然法國的王權統治終結,走入共和,鳶尾花卻從代表王室威權的存在,變成屬於全法國民眾的印記,法國人喜歡鳶尾花的純潔,同時因為經歷過這段波折,法國人對它的喜愛更勝以往,鳶尾花就好像法國的足球史,一開始似乎缺乏氣勢,但是在經過風雨與融合之後,才逐漸綻放其中的美麗與優雅。

▲鳶尾花象徵著光明和自由,原先代表王室威權,後來則變成屬於全法國民眾的印記。圖為梵谷畫作《鳶尾花》(圖/維基百科)
世界盃的老祖宗
雖然英國是現代足球的發源地,但是說到現在大家熟悉的世界盃,絕對是法國人的傑作,1904年國際足總(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簡稱FIFA)在巴黎成立,首任主席是法國籍的古林 (Robert Guérin),創始會員包括了法國、比利時、丹麥、荷蘭、瑞典、瑞士,還有當時尚未建立足協組織,而是派遣皇家馬德里足球俱樂部代表出席的西班牙,這也是足球走向國際化的開始。
FIFA的第三任主席,同樣來自法國的雷米(Jules Rimet),則是改變了足球在全球的地位,他在1930年創辦了世界盃足球賽,雖然早期的比賽遭遇到不少困難,但是世界盃的存在,讓足球獨立於其他所有運動,重要性甚至超越奧運會,雷米在位33年的努力功不可沒,而世界盃最早的獎盃,也因為他偉大的貢獻,而命名為雷米金盃。

▲法國人是世界盃足球賽的創始國之一。(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冠軍獎盃的旁觀者
雖然法國人在世界盃的發展上不可或缺,但是卻始終跟冠軍沾不上邊,直到1958年,世界盃史上最偉大的射手方丹(Just Fontaine)出現,一個人改變了法國隊的局面,他的世界盃處子秀就演出帽子戲法,最終將法國隊一路帶到季軍,他在6場比賽中攻進了13球,至今仍然是世界盃單屆進球最多的紀錄保持人,那一年的世界盃,有一個十八歲的少年技驚四座,幫助巴西拿下了世界盃的冠軍,這個名為比利的少年,在當屆也不過只攻進了6球。
1982年與1986年世界盃,法國再度出現改變法國足球歷史的巨星,那就是大家後來都很熟悉的普拉提尼(Michel Platini),這名全能的中場球員,除了贏得國史上首度的歐洲盃冠軍,更是兩度將法國隊帶進了世界盃四強,在足球史上有兩個最著名的球王,當年比利搶走了方丹的光芒,而馬拉度納則是擋在普拉提尼的面前,法國隊在狀態最好的時候,卻不幸碰上的是兩名球王統治足球的年代,讓他們始終未能觸摸那原本是由法國人建立的王座。

▲方丹至今仍是世界盃單屆進球最多的紀錄保持人。(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種族大熔爐的活力
1998年法國第二度主辦世界盃,這次他們有了完全不同的背景,在經過20年的廣納移民之後,法國成了一個外來人口超過10%的國家,這些移民為法國帶來了龐大的勞動力,對於足球來說,更是注入了一股新血,不同語言、文化、生活習慣,難免產生衝突,但是足球是一種共通的語言,不會因為你的膚色而影響你的技術,除了是融入與溝通的橋樑外,在足球事業上的成功,還可以為生活艱困的移民子弟帶來富裕的生活。
法國特有的浪漫也是一個重要關鍵,法國人的足球不拘泥於形式,對於球員的培養,更多的是開放與自由想像,這也讓不同種族的球員,得以散發自我的天性,各種獨特的性格最後終會形成一個共同的樣貌,而不是無法相容的混沌。
法國國家隊逐漸成長為3B球隊,也就是黑人(Black)、白人(Blanc)、阿拉伯人(Beur)所共同組成,在1998年的那批巨星中,有塞內加爾血統的維耶拉(Patrick Vieira)、迦納血統的德賽利(Marcel Desailly)、法屬西印度群島血統的亨利(Thierry Henry)與圖拉姆(Lilian Thuram)、阿爾及利亞血統的席丹(Zinedine Zidane)、新喀里多尼亞血統的卡倫布(Christian Karembeu)、阿根廷血統的特雷澤蓋(David Trezeguet)、波蘭、亞美尼亞及蒙古游牧民族血統的佐卡耶夫(Youri Djorkaeff)、巴斯克血統的利薩拉祖(Bixente Lizarazu),可以說,法國靠著全世界贏得了世界盃。

▲移民為法國足球注入了一股新血,如知名球星席丹(右)具有阿爾及利亞血統,姆巴佩的父親則是移民至法國的喀麥隆人。(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源源不絕的新鮮力量
雖然許多球員已經是移民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理論上不應在去深究每個球員的血統,但很明顯的是,法國隊的組成依然倚靠來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子弟,在歐洲經濟發展腳步放緩之後,許多右派團體崛起,各國開始反對接納過多的移民,法國當然也不例外,在國家隊甚至發生過總教練布蘭克(Laurent Blanc)與隊職員討論國家隊中「真正法國人太少」的議題,而遭到各界抨擊,這也導致許多不同族裔的法國球員,轉而效力自己父母或是祖父母的國家隊。
不過這並沒有讓法國的足球發展停滯,2018年法國隊贏得他們的第二座世界盃冠軍,法國一直有歐洲最好的青少年培訓計劃,法甲聯賽體系成熟,也是非洲球員進入歐洲的入口,雖然表面上有一些種族歧視的言論,然而法國隊成為世界隊的趨勢,是不可能阻擋的,法國的足球人才,至今依然源源不斷的出現,法國隊唯一的問題,是這麼多的天才球員,彼此能不能和平相處,這是別人想要,卻無法擁有的煩惱。

▲法國可說是非洲球員進入歐洲的入口。(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喚醒世界的高盧雄雞
高盧雄雞是法國體育圈重要的象徵,包括奧運會與足球國家隊,乃至於橄欖球、擊劍、射箭、冰球等協會的吉祥物,都是雄雞,其實一開始這並不是一個好聽的稱呼,古羅馬人稱如今法國一帶的為高盧地區(Gallia),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為高盧人(Gallus),而Gallus在拉丁文中有公雞的意思,周邊幾個國家的人,以此來嘲諷高盧人如公雞般好鬥,但是高盧雄雞這個稱號,在16世紀之後,卻漸漸為法國人所喜愛,因為公雞在法蘭西文化裡,也有驍勇善戰和精力充沛的意象。
法國大文豪雨果曾經寫下這樣的詩句:
「Mais c'est le coq gaulois qui réveille le monde:
Et son cri peut promettre à votre nuit profonde
L'aube du soleil d'Austerlitz!」
「但是喚醒世界的是高盧雄雞:
牠的啼聲可以向你深沉的黑夜
允諾奧斯特利茨太陽〔照耀〕的黎明!」
奧斯特利茨位於捷克境內,是當年拿破崙擊敗俄羅斯與奧地利聯軍的地點,瓦解了第三次反法同盟,雨果對於高盧雄雞可以為法國帶來勇氣與希望深信不疑,世界盃是法國人所創造,卻曾經一度遠離它,在經過長期的低迷之後,終於有了閃耀的黎明。
法國人一直有著截然不同的精神寄託,雄雞與鳶尾花,堅毅與浪漫,渴望勝利與追求雅致,但其實兩者並不衝突,它們共同造就了今日法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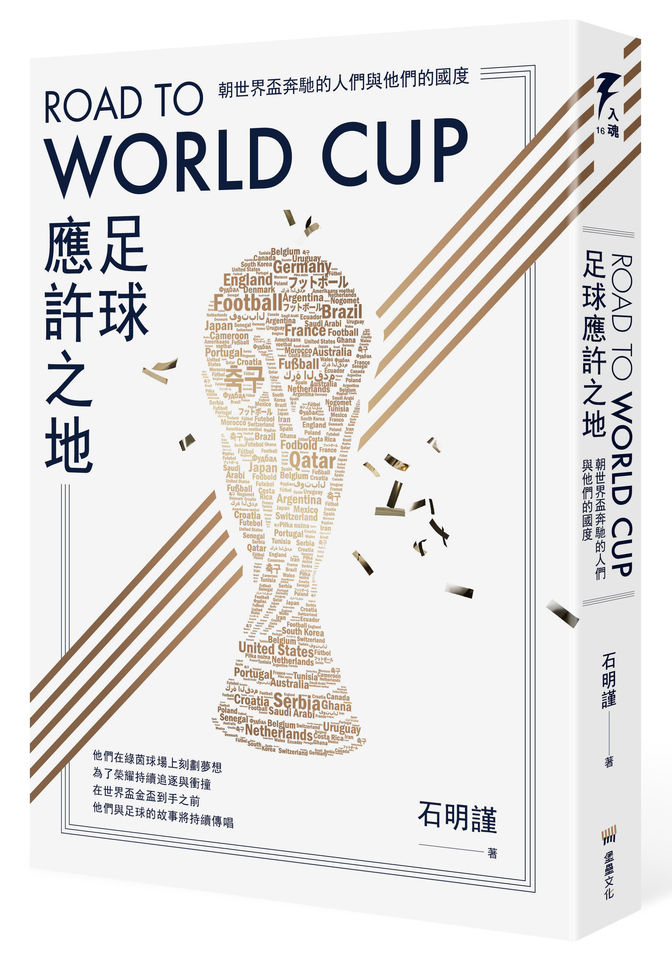
▲石明謹著,《Road to World Cup足球應許之地:朝世界盃奔馳的人們與他們的國度》,堡壘文化。(圖/堡壘文化提供)
熱門點閱》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摘自《Road to World Cup足球應許之地:朝世界盃奔馳的人們與他們的國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歡迎投書《雲論》讓優質好文被更多人看見,請寄editor88@ettoday.net,本網保有文字刪修權。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