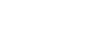檸檬小編這麼說
娜迪雅‧穆拉德是居住在伊拉克境內克邱村的一名普通亞茲迪女孩。
2014年,伊斯蘭國(IS)入侵了克邱,俘虜了包括21歲的娜迪雅在內的女孩們,
她們被迫成為薩比亞(Sabiyya,意即性奴)、家人被殺害,
自己則被伊斯蘭的聖戰士們任意凌虐和轉賣……
文/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2016年諾貝爾獎提名人)、珍娜‧克拉耶斯基Jenna Krajeski
譯/洪世民
哈吉.薩曼一再告誡我:「如果你試圖逃跑,我會懲罰你。」但從未確切表明會怎麼懲罰。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他會打我,但他之前也不是沒打過我。薩曼無時無刻不打我。不喜歡我打掃房子的方法會打我、工作不順心會遷怒我、如果他強暴我時我哭出聲或閉眼睛也會打我。
也許,如果我試圖逃跑,毆打會嚴重到讓我傷痕累累或毀容,但我不在乎。如果傷口能阻止他或其他人繼續強暴我,我甘之如飴。
有時在他強暴我之後,他會告訴我根本沒必要試。「你不再是處女了。」他會說:「而且你是穆斯林了。你的家人會殺了你的。你毀了。」儘管我是被逼的,但我相信他。我覺得自己毀了。
我想過各種讓自己變醜的方法,在中心,女孩會在臉上塗灰抹土、把頭髮弄亂,也不洗澡,想讓臭味逼退買主。但我除了拿刀劃臉或剪光頭髮,想不到其他辦法,而我覺得割臉或剪髮都會招來一頓毒打。如果我給自己毀容,他會殺了我嗎?我覺得不會。我活著還是比較有價值,而且他也明白,死是一種解脫。我只能憑空想像假如我試著逃跑,薩曼會對我做什麼。

▲▼娜迪亞及其家人(圖/時報出版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

然後有一天,測試的機會來了。
那天晚上,薩曼帶兩個男人回家,都是我沒見過的好戰分子,沒帶薩巴亞(編按:Sabaya,薩比亞的複數型態)同行。
「你打掃完了嗎?」他問,我說掃好了,他就叫我回我們的房間過夜,一個人。「廚房裡有食物,如果你餓了,就叫胡珊,他會拿點吃的上去。」意思是要我離開他們的視線,在房裡等他。
不過,他叫我先給他們倒茶。他想炫耀他的薩比亞。我照他說的去做,穿上他喜歡的一件洋裝,把茶從廚房端到客廳。一如以往,那些好戰分子在聊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勝利。我注意聽他們有沒有提到克邱,但完全沒聽到關於家鄉的事。
客廳擠滿男人,其中只有兩個是訪客。看來這中心的衛兵全都去和薩曼及客人一起用餐,自我來此後第一次離開崗位。我懷疑那是不是他堅持要我在房裡待到客人離開的原因。如果衛兵通通跟他們在一起,那就表示沒有人巡邏庭院,也沒有人在浴室外監視以確定把門關上的我不會試圖從窗戶爬出去。門外不會有半個人聽見裡面發生什麼事。
端完茶,哈吉.薩曼把我打發走,我便上樓去。計畫已經在我腦中成形,而我動作很快,知道如果我停下來思考,可能就會說服自己放棄,而像這樣的機會也許不會有第二次。
我沒進房間,直接走進一間客廳,我知道那裡的衣櫥裡仍塞滿亞茲迪女孩及這間房子的前屋主留下來的衣服。我開始尋找多出來的罩袍和面紗。我很快找到罩袍,趕緊套在我的洋裝上。為遮住我的頭髮和臉,我綁了一條黑色的長巾代替面紗,希望在我到達安全的地方之前,不會有人發現箇中差異。然後就往窗戶走去。
我們雖位於二樓,但不算太高,而且窗戶下面的牆面,有些沙色的磚塊砌得凸出幾吋。這是摩蘇爾常見的設計,除了裝飾沒有其他意義,但我認為那些磚塊或可做為往下爬到庭院的梯階。我把頭伸出窗戶,尋找平常隨時都在庭院走動的衛兵,但院子空無一人。有個油桶靠著籬笆放,再完美不過的梯凳。
庭院圍牆的外面是車聲隆隆的公路,但隨著大家紛紛進屋裡吃晚餐,街上的人開始少了,而我想在薄暮中,比較不會有人注意到黑頭巾不是正統的面紗。但願我在被發現之前找得到人幫我。除了塞在胸罩裡的珠寶和我媽的配給卡,我把一切都留在房間裡了。
我小心將一腳伸出窗外,再換另一腳,待下半身出了窗外,軀幹還在裡面時,我挪動雙腳,試著去踩那些凸出的磚塊。我的手臂在抖,但我緊抓窗台,很快讓自己穩定下來。我感覺得出,這樣爬下去不算太難。
就在我開始尋找下面的磚塊時,我聽到下方傳來一聲槍響。我凍住,身體掛在窗台上。
「進去!」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底下對我大叫。
我沒有往下看,馬上用力把自己撐起來,穿過窗子,落到窗下的地板,害怕得心跳加速。我不知道是誰看到我。哈吉.薩曼的所有衛兵都跟他一起在客廳。我在地上縮成一團,直到聽見腳步聲走向我,我抬頭,看到哈吉.薩曼站在眼前,便以最快的速度衝回房間。
門開了,哈吉.薩曼進來,手裡拿著鞭子。我放聲尖叫,跳上床,拉了一件厚被子遮住全身和頭,像小孩那樣躲藏。薩曼站在床邊,不發一語,開始鞭打。鞭子下得又快又狠,怒氣騰騰,厚重的毯子幾乎保護不了我。
「給我出來!」哈吉.薩曼大吼,我聽過他最大的聲音:「給我離開毯子,衣服脫掉!」
我別無選擇。我掀開毯子,看到薩曼仍拿著鞭子站在面前,慢慢脫掉衣服。當我一絲不掛後,我一動不動地站著,等待他要對我做的事,默默哭泣。我以為他會強暴我,但他開始朝門口走去。
「娜迪雅,我告訴過你,如果你試圖逃跑,後果不堪設想。」他說。他輕柔的聲音回來了。然後他打開門,走出去。
一會兒後摩提賈、亞希雅、胡珊和另外三名衛兵走了進來,盯著我看。他們站的地方,就是片刻前薩曼站的地方。我一看到他們,就明白我的懲罰是什麼了。摩提賈第一個上床。我試著阻止他,但他太強壯。他把我推倒,而我什麼都做不了。
在摩提賈後,換另一名衛兵強姦我。我大聲呼叫我媽和我哥凱里。在克邱,每當我需要他們時,他們就會出現。就算我是犯蠢而吃苦頭,只要我呼叫,他們還是會來幫我。在摩蘇爾,我孤單一人,而他們的名字,是他們唯一留給我的東西。不論我做什麼、說什麼,都無法阻止那些男人侵犯我。
那晚我記得的最後一個畫面是其中一個衛兵的臉。我記得在輪到他強姦我之前,他摘掉眼鏡,小心放在桌上。我猜他是擔心眼鏡會破吧。
當我在早晨醒來,我獨自一人,全身赤裸。我動彈不得。有人,我猜是其中一個男人,幫我蓋了條毯子。我試著爬起來時,頭暈得厲害,伸手拿衣服時,身體痛得要命。每一個動作感覺都像要把我推回不省人事,彷彿一道黑色簾子在我眼前拉了一半,這世界的一切都成了本身的影子。
我進浴室沖個澡。我身上盡是那些男人留下的髒污,我打開水,站在底下很久很久,哭泣。然後我把自己徹徹底底洗乾淨,用力擦洗身體、牙齒、臉、頭髮,從頭到尾都在祈禱,求神幫助我,原諒我。
然後我回到房間,躺在沙發上。床上,強暴我的男人的氣味久久不散。沒有人進來看我,但我可以聽到他們在房間外面說話,過了一會兒,我睡著了。我什麼都沒夢到。當我下一次睜開眼,薩曼的司機正站在我旁邊,戳我的肩膀。
「娜迪雅,起床,起來,把衣服穿好。」他說:「該上路了。」
「我要去哪裡?」我問,把我的物品塞進我的黑色袋子。
「我不知道──總之是離開這裡,」他說:「哈吉.薩曼把你賣了。」
*延伸閱讀:北京窮人「只配住老鼠窩」 樓上夜店在狂歡...60人擠在惡臭地穴
*本文摘錄自《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
作者: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珍娜‧克拉耶斯基Jenna Krajeski
譯者:洪世民
本文由 時報出版 授權轉載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