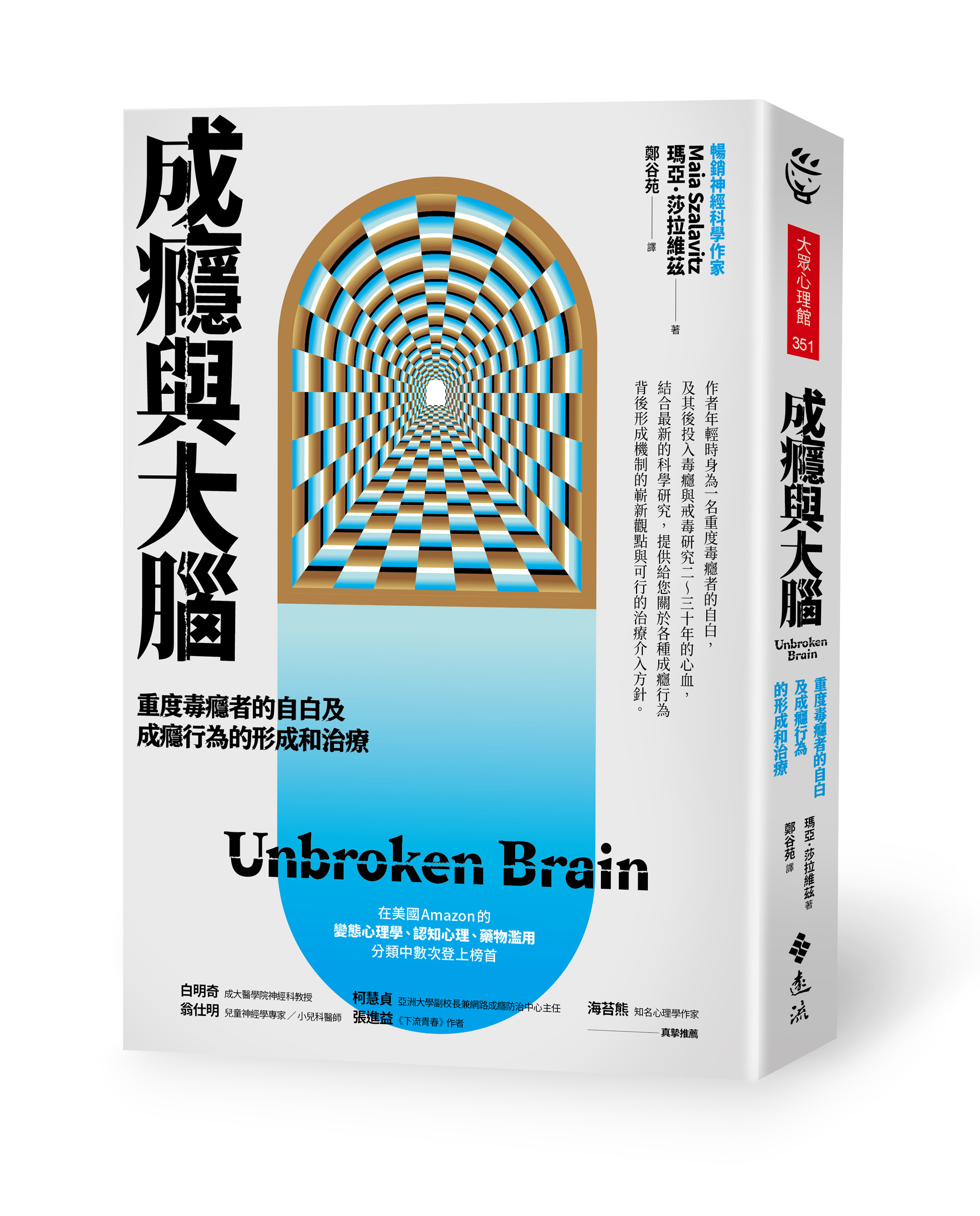文/瑪亞.莎拉維茲
譯/鄭谷苑
被哥倫比亞退學後不久,我開始研究海洛因,就像我對之前使用過的其他任何藥物一樣。
我讀《赤裸的午餐》(NakedLunch)(註1)。我一再的聽「地下絲絨」(TheVelvetUnderground)(註2)的歌:〈海洛因〉……〈等待那個人〉……〈芮姐妹〉。盧‧瑞德(LouReed)粗獷的聲音,歌詞詳細的描述了毒品和針頭的嚴重後果,而他的語調和音樂背叛了他們對注射藥物的狂喜和愛。
「這是我的妻子/這是我的生命……」我過去一直說永遠不會嘗試海洛因,因為我知道我會愛上它;但是現在我已經不在學校了,而我的人生基本上也已經完蛋,我開始想反正我也沒有好損失的。
我會去卡爾頓找麥特,而我和他有著折磨人的關係。最開始,我的古柯鹼關係人是伊森,麥特是我這名高中男友的哥哥。當伊森決定戒掉古柯鹼時──當時我是哥倫比亞的大一新生──他就給了我他哥哥的電話,這樣我就不會同時失去我的事業和男友。
麥特和我大約一年後開始交往。那時候,他和他女友蘇珊正在「休息時間」,而我是單身。在我大一那年我們剛見面時,麥特住在一個拉法葉街上的小社區中的舒適公寓,裡面滿滿是他收集的,數以百計的爵士、搖滾、放克和迷幻唱片,還有書籍,和最特別的是漫畫書,或是他們當時開始稱呼為「圖像小說」。

▲藥物、毒品示意圖/示意圖/pixabay
那個時候,他是整個低調運作的地下毒品網路的中心,從四分之一公克到四分之一公斤,從死之華和爵士樂手到電影工業中的技術人員、音效工程師、大學生、女商人和華爾街的交易員,各種包裝大小、各行各業的人他都賣。
高高瘦瘦、棕色頭髮、留著八字鬍,有著調皮的眼睛,他熟諳當時我很愛的事物:迷幻音樂和毒品。這一切都讓我入迷。但是,雖然我當時並不了解,當我們開始約會時,麥特已開始漸漸成癮了。他不能決定到底是要我還是蘇珊。
而我當時還在擔心自己沒人愛,我的男友沒有對我說過「愛」這個字──的確,就像伊森,他們通常會不斷告訴我的是他們並不想許下什麼承諾,以及我基本上不是什麼妻子的料。不過,至少我可以讓麥特和我上床。
然而,由於關係脆弱又不確定,我試圖利用我們之間的毒品管道,不只是向他購買毒品,同時也利用我們用來聯絡毒品交易的呼叫器監控他。通常,當我呼叫他時,我的確是需要安排毒品的交易,但我也試著藉此知道他的行蹤,防止他消失到某個「祕密的」、無節制的行為中。找不到他,會讓我無法提供客戶的所需。當然,我也不想讓他有任何機會去見蘇珊。
我對異性交往,就像對古柯鹼一樣癡迷和受到某種力量的驅使,一如我之前所有的強烈興趣。同時,我也無法脫離1980年代流行的呼叫器,我每天一醒來就把它戴上,一如後來沒有電子郵件或推特就不行。

▲被退學後開始對海洛因成癮/示意圖/pixabay
就像古柯鹼本身,麥特正是一種間歇性增強──他的不可預測性和混亂的魅力讓我會去猜測,讓我拚命的想找出某個隱藏的模式讓他愛我。就是這個關係和古柯鹼這兩件事讓我當天來到了卡爾頓。
在這個時間點,麥特和我同居在哥倫比亞附近,113街上的一間公寓裡。我們已經從吸食古柯鹼變成用抽的;這正是在快克古柯鹼變成新聞頭條之前的事。事實上,在快克古柯鹼引起集體驚慌反應之前,上千的紐約客早就開始用加熱的方式在吸食了。
1984年,在從百老匯街延伸出去的96街和哥倫比亞位在116街的大門之間,就有十幾間酒窖,以提供玻璃快克古柯鹼菸斗、金屬孔網、迷你火焰噴槍做為招攬生意的特色,有時候會藏在櫃檯後面,甚至有的明明白白地放在窗戶邊。其他地區也有類似店家的聚落,而且很快的,很多角落就都有了快克古柯鹼的藥頭。
到了1986年,網路和報紙好像用他們誇張的說法,說快克古柯鹼是有史以來,最令人害怕、最強和最會上癮的藥物,來幫毒品行銷。雖然這些說法對一般人來說沒什麼賣點,但是對那些追求極端經驗的人──很多最有上癮風險的人──這些說法傳遞出來的訊號,是這種藥物一定能夠提供很強而有力的刺激,也是終極的禁果,這兩點對他們來說都是極具吸引力的。
在1988年總統大選的暖身階段中,主要的新聞類雜誌和全國性報紙上,大約有一千則報導裡有快克古柯鹼和古柯鹼出現;單單NBC,在11月之前的七個月期間就有難以置信的十五個小時的節目在講這些故事。但當時,我們這群人中,很多多年以來早就可以利用蘇打粉、古柯鹼和水來自製這些產品了。我們不認為加熱後吸食的毒品會讓你變成怪物;然而,我們當然知道這會讓事情變得更怪異。
這就是為什麼如果要加熱毒品來吸食,我喜歡在家裡做。這種嗨法是很耗費精力的;至少媒體在這方面是說對了。一旦你開始吸食,接電話或是應門這類的干擾,或是最糟的得要出門去做什麼事,都是令人無法忍受的。一旦你處在很嗨的狀態,環境中的任何非預期因素都讓人覺得恐怖。
連音樂都很棘手:這也可能要歸功於1980年代讓新世紀(New Age)音樂廣受歡迎的音樂公司溫德希爾(Windham Hill)(註3) 的產品,在加熱吸食毒品的過程中,他們的音樂毫無爭議的是很有用的背景音樂。其中,「幻影傳真」(Shadowfax)(註4) 就是我這時的首選樂團。
同時,如果吸入古柯鹼可以提供一種間歇性的增強效果,加熱吸食就糟糕多了。有時候,你可以用火焰槍把它融化成完美的、帶有甜味的、有化學香味的白煙,誘人的蜷曲在菸斗的圓形斗部,然後把你炸入同溫層中,至少可以持續個幾分鐘。有時候,你會隨著毒品產生妄想,或只是麻木的渴望再來一劑,再一劑就好,然後再一劑,這樣就好了。
夜晚通常就在「再一劑」的控制下,溶解成為白日。最糟的部分,就是毒品統統被用完了,拚命的再搜尋任何一丁點你剛剛可能漏掉的藥品,吸食任何從地板或地毯上找到的小殘屑,只為了萬一裡面有殘留的、加熱過的毒品。
跟我不一樣,麥特喜歡不在我們的公寓裡吸食加熱毒品,他愛在各家破爛的廉價旅館,似乎越骯髒越好。他偏好和比他藥癮更嚴重的人一起吸食古柯鹼;諷刺的是,此時此刻,我的成癮狀態讓我被排除在外。我通常還有辦法結束我的狂歡來盡我的責任,即使只是勉強做到。
有一次,只是為了表示他對毒品的掌控權,麥特把幾塊加熱過的結晶丟出卡爾頓的窗戶外,類似有錢人在有乞丐時丟出百元大鈔。和他一起吸毒的不是多有尊嚴的人,他們披著床單爬下樓來到庭院裡,試著取回那些毒品,還向鄰居解釋他們是在尋找一些「珍貴的石頭」。麥特自己沒有降格到這種程度──不過他也不需要,他總是可以拿到更多。

▲從吸食古柯鹼變成用抽的/示意圖/pixabay
在那個1985年的下午──對我們來說正是早晨,因為我們很少在11點以前起床──當我找不到麥特時,不知怎地,我知道他正和蘇珊在一起。我在輸入的回電號碼之後加上119,表示這是和工作有關的緊急事件,在不斷地呼叫他仍然持續得不到任何回應之後,我決定自己找到他。
我打了卡爾頓的共用電話──電話裝在走廊上,而旅館服務人員一般會知道誰在那裡,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起身滿腹牢騷的叫對方來接電話──而發現他正在那裡。
就在我到達之前,他剛剛賣了一些古柯鹼給一對神智非常恍惚的毒蟲,我只知道他們叫做巴布羅和吉吉。她有長長的、直而骯髒的金髮,大大的圓眼鏡,手背和腿上布滿小小的痂,而她是這樣解釋的:「我摳這些傷口是因為我吸毒;我吸毒因為我摳。」而他有長長的黑頭髮,深陷的棕眼,身材苗條,看起來也只比她好一點點。
他們賣海洛因來維持自己的用毒習慣,同時,由於某個奇蹟,剛剛拿到了兩盎司的最高級的「中國白」(China White)。既然麥特身上很可能至少有一盎司的古柯鹼,在這個只有床(沒有衛浴或廚房),一天租金35美元的單人房裡,家具不穩固,龐克式的裝潢,還有不平的地板,這裡有時候有價值數千元以上的毒品。如果我們被抓到,在洛克斐勒條款之下,每個人都很可能要被判15年徒刑到終身監禁。
因為這樣,大家最不想要的就是大聲叫罵,因為這有可能引來我們不想要的管理員的注意,或是更糟的情況。所以,當我開始刺耳的向麥特大聲的表達我對蘇珊的不滿時,巴布羅或是吉吉很快地就切了一條海洛因拿給我。
我想都沒有想,在暴怒之下就吸了。我一次就吸了兩條海洛因粉,就好像我一輩子都在吸食海洛因似的。突然間,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完美的、幸福的寂靜。我不再在乎蘇珊了,我甚至連麥特也不在乎了。我什麼都不在乎了,我什麼東西、什麼人都不需要了。
那是一種完全的滿足。所有的慾望都消失了。是一種立即的涅槃。在物質的感官上,感覺像是被某個極度柔軟、溫暖舒適,環繞著你的東西重重的擊中了。我身體裡的每個分子都受到呵護。我回家了。雖然我覺得噁心並跑去廁所,但我根本沒有吐出來。
海洛因給我別種毒品只能搔得我心癢癢的舒適感,一種讓所有擔心都遠離的幸福感。那種嗨不是很精巧;不像大麻、迷幻劑、甚至古柯鹼那樣,會帶你進入黑暗。在海洛因中翱翔,我覺得很安全,被包覆在一床舒適的安全毯中。
雖然很多人認為這種緩衝感令人不安──甚至是一種令人不愉快的麻痺感──對我而言,卻覺得終於找到一種我一直以來就需要的隔絕感。感覺像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我真的感到安全,和被愛。
註1:《赤裸的午餐》(1959)是美國作家威廉‧柏洛茲(William Burroughs) 的長篇小說,內容為毒癮者威廉‧李的自述。本書入選《時代》雜誌評選的「1923~2005年百部最佳小說」。
註2:「地下絲絨」是一個活躍於1960~70年代的美國搖滾樂團,影響了許多後來的搖滾樂團與歌手。
註3:溫德希爾是一家獨立唱片公司,主要是發行演奏音樂。公司在1976年成立,在80、90年代非常受歡迎。
註4:幻影傳真是一支1970年代芝加哥的室內爵士/新世紀/電子音樂的樂團。最有名的專輯是《幻影傳真》和《核子村莊的民歌》(Folksongs for a Nuclear Village),1989年以後者獲得葛萊美獎。
*本文摘錄自《成癮與大腦:重度毒癮者的自白及成癮行為的形成和治療》
作者:瑪亞.莎拉維茲
譯者:鄭谷苑
本文由 遠流出版社 授權轉載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