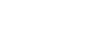「世界是一本書,不旅行的人只讀了一頁。」許多人樂意表示自己熱愛旅行,在工作忙碌之餘,給自己一個喘息的空檔。旅行不只能讓人脫離日常生活的軌道,更是現代人生活品味的表現,表示自己還有多餘的時間和金錢,能品味不同國度的地貌與文化風情。
但你一定想像不到,在19世紀說出「我喜愛旅行」會被認為有精神疾病!當時的精神科醫生分析過幾個特殊病例,就將全部喜愛旅遊的人定義為「衝動控制失調」,或者稱乎他們有「旅遊癖」或「漂泊狂」(wanderlust)。和偷竊癖、縱火狂、酒精沉癮等類似,而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強制關起來,再用鞭子毒打一頓。被這樣對待的人,誰還敢說自己想旅行?也許這就是「治療成功」的原因吧。
這段歧視旅遊喜好者的由來,特別在1886年至1909年期間被大做文章,醫學界驚覺這類喜愛旅遊的「傳染病」在法國蔓延開來,數十位男性發現自己在精神恍惚的狀態下漫遊歐洲,心裡明明沒有確切的目的地,人卻不自覺地旅行至幾百公里的遠方。這些人的下場都被警方拘留,或在異地被抓進精神病院,簡直人間蒸發。
當時的醫學紀錄聲稱,這些「喜愛旅遊」的人,心裡有停不下來的欲望。可能是迷戀遠方國度的風景、想去曾經在某本書中見過的地方,亦或者是安撫埋藏在心裡的鄉愁。他們渴望踏上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徑;冀望在黎明破曉之際,在某個湖畔邊聽見自己的聲音。

▲那些「喜愛旅遊」的人,心裡有停不下來的欲望。(示意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歷史上第一位「漂泊狂」
記載中首位罹患旅遊癖的患者,叫做亞伯特.戴達斯,來自波爾多的瓦斯裝配工人。他曾徒步穿越法國,後又自行前往莫斯科及君士坦丁堡。1886年因為身體虛脫而入院治療。照顧他的精神醫師診斷戴達斯為「漂泊狂」,難以克制旅行的衝動。且醫生發現戴達斯只能在催眠狀態下,才能回想起自己的瘋狂旅行。
在醫生對戴達斯下了診斷後,社會上突然出現了一大堆同樣病例。這些人都是男性,且大多是貧窮的工人。他們乾淨整潔,不愛出風頭,默默在崗位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卻不約而同的辭職不幹,離開家鄉前往遠地甚至其他國家,在當地打工謀生long stay,過上幾個月至一兩年的時間,住膩了就再度踏上旅途,移動到下個陌生他方。
這些人是突然出現的嗎?當然不,僅不過是當時的醫學界、貴族、掌權的公務員們,突然意識到社會上多了這麼一群不想終身待在家鄉「老實生活」的年輕人。19世界後半社會變遷與多次戰事帶來的壓力,移動式的生活,在平民階級早吹起了風潮。

▲在19世紀的法國,患有旅遊癖的人會被送進精神病院。(圖/翻攝自Science Museum)
愛旅行會被社會唾棄
19世紀間,歐洲經歷了一連串勞工階級發起的武裝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也讓勞動階級的工人們,陷入日復一日的枯燥勞動。同時,他們還得擔心隨時可能被國家徵兵,死在戰場淪為孤魂。年輕一代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方法,於是嘗試移動到遠方,試圖讓旅遊,亦或者說「漫遊」成為治療苦悶的良藥。
當時法國的社會,認為「旅行、流浪」是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懦夫行為,所以這些成天都想遠走他方的人們,都被診斷為精神失調。上流階層定調了男人應當待在家裡,做個顧家的好男人(女人連被提起的份都沒有)當時也為了防範徵兵找不到人,各國施行嚴苛刑罰對付逃兵,讓許多男人心生恐懼,逃走的想法越發堅定。
面對種種束縛,他們抓住了「漂泊狂」這根救命草,在漂泊的同時,某種程度也算脫離社會的枷鎖,找回心靈上的自由。換句話說,不論是有意、無意的不間斷旅遊,正是對社會的一種「不妥協」。
時至今日,旅遊癖不再是「癖」,脫去了病態框架,喜愛旅遊是一種個人志向,且成為一種令人嚮往、有吸引力的標誌。你會在交友平台上寫著:「興趣:旅遊」,把旅遊當作個人標籤,讓別人知道你是個懂享受生活的人。
喜歡旅遊的人都知道,在異國土地上,時間彷彿緩下腳步,空氣嗅起來似乎也浪漫。對當時的人來說,毫無目的的漫遊看似無可救藥,但卻是逃離現實的方法;對現在的我們來說,旅行某種層面也是逃脫現有的生活模式,讓我們得以在忙碌奔波的人生時鐘裡,有個時間好好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