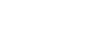日本政府在2月1日正式將新冠肺炎(COVID-19)列為「指定感染症」,會以公費治療患者,不分國籍與簽證,必要時會強制病患住院,以穩定疫情。雖然看起來像是很有善心的措施,但那些在日本沒有身份打黑工的人,是不是就算感染了也不敢就醫呢?有沒有可能也變相地成為防疫的漏洞呢?
--

▲早期的歌舞伎町是黑工們的大本營,如今經過掃蕩後,已經減少許多。(圖/魚漿先生提供,請勿隨意翻拍,以免侵權,下同。)
前陣子看到日本跟台灣的感染人數不時增加,心裡不免擔心了起來。一方面是擔心日本這邊大規模傳染,另一方面更是擔心台灣這邊醫護人員過度勞累。心裡鬱悶的我一直想找個機會喝一杯,便問了從事納棺師的小李有沒有空。恰巧他臨時有事找我,我們就一樣約在歌舞伎町的小酒吧聊聊。
剛一見面,小李就從包包拿出了一捆口罩給我。由於小李的公司是處理喪葬相關的事務,本來就有預備一些口罩。因此在這個非常時期,老闆特地把這些口罩拿出來給需要的人,只送不賣。
我憶起中國人大量購買日本口罩帶回中國的光景,就不經意地想到我跟小李都認識的一個中國同學「老鄭」,因為他在唸書的時候就專門做這些掃購日貨轉賣的偏門生意,我便跟小李聊起了他。
「老鄭前年死了。」小李這樣淡淡地說。
聽到老鄭死訊的我震驚的說不出話來,就連正在寫文章的我到現在還不太能接受。我趕緊放下酒杯,繼續追問老鄭是怎麼死的。

▲我跟小李還有老鄭,曾在畢業的前夕來這裡喝上一杯。
由於我是三十多歲才來到日本念語言學校,說真的像我這麼老還來念語言學校的人不多。而老鄭比我年輕一兩歲,同樣是相似年齡的我們很快就變成了好朋友。老鄭那時候的出勤狀況並沒有很好,聽說他在打工,薪水很不錯,一天甚至可以有三萬日幣。
「你還記不記得大前年的時候,我們一起在新大久保居酒屋的那一晚?」小李問。
我點點頭,想起了那天的光景。那天剛好是我們畢業的前幾週,老鄭便約我們一起喝上一杯。在席間老鄭意氣風發的說他想留在日本打工,不想回中國了。
「賺大錢哪裡需要什麼身份?我決定畢業後就留在日本打黑工啦,哈哈哈~~」老鄭笑著說。
我連忙跟小李要他不要講那麼大聲,畢竟大久保有很多聽得懂中文的人。不過老鄭要我們別擔心,因為那時候他還有學生身份。後來老鄭就在日本人間蒸發了,連畢業典禮也沒有來。電話也打不通,學校也跟日本政府回報說他失蹤了。
「前年的時候,老鄭找上了我。」小李低著頭接著說。
小李再看到老鄭的時候,嚇得差點趕快想帶他送醫。那時老鄭可以說是瘦得皮包骨又痼疾纏身。原來老鄭這幾年過得並不好,他本來做的就是偏門生意,沒有了身份之後,常常被檢舉躲警察,而檢舉人往往都是老鄭的同胞中國人。

▲最近池袋變成打黑工的大本營,據說有些打黑工的中國女子迫於生計而投入風俗業。
後來老鄭離開東京,到了日本北邊打工,生活環境很差,加上沒什麼休息。好幾次差點就倒在雪地裡面起不來,加上是黑工,三不五時就被老闆辭退,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這次回到東京找小李,是因為得了很嚴重的流感,沒有錢就醫,已經發燒了好幾天,發現再燒下去可能會喪命,只好死皮賴臉的來找小李借錢。
老實說,在日本看病真的不便宜,尤其你沒健保的話,往往就要花到萬円日幣以上。也就是看一次大概是台幣三四千元,在台灣就算自費,往往都還比日本划算。所以生活在台灣的朋友,請多珍惜台灣優良且划算的醫療資源。
「那老鄭怎麼死的呢?」我問。
小李說當下就拿錢出來給老鄭急用,畢竟人命關天。後來老鄭請同樣是黑工的中國朋友帶他就醫,不過那個中國朋友卻舉報他,沒力氣的老鄭來不及逃跑被抓,隨後在日本簡單診療後就遣返回中國了,回去後不久就病死了。
「唉,至少他最後是在自己的家鄉病死的,也算落葉歸根了吧。」小李嘆口氣說。
我們兩個默默的沒說話,只悶著頭喝酒,似乎要把老鄭的份給喝回來。在這個疫情緊張的非常時期,這些在日本到處打工又沒有身份的黑工們,若是感染了武漢肺炎又不敢就醫,會不會成為防疫的漏洞呢?我想也是目前日本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