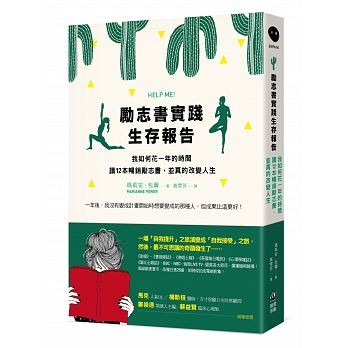文/瑪莉安・包爾
譯/高霈芬
那時我八歲,在遊樂器材區走來走去。我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上哪去了,其他朋友也都不在,總之那天我一個人。大家都期盼著午餐時間,就像期盼著週日下午一樣。
那天下了一早上的雨,灰色的水泥濕濕的,天空的雲沉甸甸的,感覺馬上又會下起大雨。世界籠罩在一片不祥的氛圍之中。有幾群小女孩分散在遊樂設施各處,有些爬上遊樂器材倒掛金鉤,深藍色的百褶裙卡在內褲縫裡;有些人在香蕉色油漆漆成的格子裡玩跳房子;也有一群人在那跳來跳去。小皮球、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
我在遊樂區四處張望,希望找到人一起玩,也許有人跟我一樣落單。落單的人比較會願意一起玩,可是沒有人落單。我看見兩個跟我同班的女生坐在長椅上聊天,她們雙腿交叉,大概是跟媽媽學來的姿勢。其中一個女生在吃洋芋片,另一個女生吃著一小盒葡萄乾。

▲遊樂區內的孩子各自開心玩耍著。(示意圖/非當事人照片/取自免費圖庫Pexels)
我好羨慕她們的點心,我今天的點心只有水果,而且我的香蕉已經快爛了。我認識她們,但沒有一起玩過。我走到她們附近晃來晃去。
「有事嗎?」洋芋片女孩問。她的名字叫露西.T,我們班總共有四個露西。露西.S、露西.W、露西.J還有露西.T。T聰明伶俐,姊姊也在同一間學校,所以她算風雲人物。她留著一頭狂野的灰褐色頭髮,髮量相當豐厚,髮帶根本繞不了第二圈。她和露西.J坐在一起,J有著絲綢般滑順的棕色頭髮,說話聲音非常溫柔。J也有個姊姊,他們家放假會出國玩,所以她的文具都來自義大利或法國,這兩點是她的雙重優勢。歐洲大陸進口的小網格筆記本是一個班級中的最高榮耀。
「可以跟妳們一起玩嗎?」我脫口而出。
話一出口,我便擔心這種問法聽起來太落魄又太幼稚。我已經八歲了,不是「玩」的年紀了。我怎麼不說:「可以跟妳們一起坐嗎?」或是「可以跟妳們聊天嗎?」這個失誤揮之不去。兩個女孩面面相覷。

▲小女孩擔憂自己說出來的話太幼稚。(示意圖/非當事人照片/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
「我們要考慮一下。」葡萄乾露西說。
「妳可以先後退幾步嗎?我們先討論一下。」洋芋片露西說。
我退了幾步,假裝盯著一棵大櫟樹看。上學期我們從這棵大櫟樹的樹枝上取下樹葉,先在紙上描了樹葉的邊,然後再把樹葉放到書裡壓乾。我們還畫了橡實,摸了大樹的樹皮。多希望我能跟這棵樹玩就好。
「妳可以回來了。」葡萄乾露西說。我走向她們。
「妳今天不能跟我們玩。」洋芋片露西說。她說得清清楚楚,沒有遲疑。
「明天也許可以。」葡萄乾露西說話時,臉上硬擠出了一抹微笑,可能她覺得這樣對我有點壞。
「好喔,謝謝。」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謝謝她們。可能是因為她們有花時間考慮吧。
離開她們的時候,我低頭看著自己的灰色Clarks皮鞋,我感覺自己的臉頰越來越燙,眼睛開始刺痛。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但我還是哭了。我跑到廁所,關上門,一路哭到上課鐘聲響起。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個被拒絕的記憶。雖說在那之後我並沒有太常想起這一天,但在往後的人生中,我可能也是花了不少時間在逃避約人一起玩卻被拒絕的這一刻。只要聽到「不能」這兩個字,我就會覺得自己一秒變回了八歲。

▲現在的她只要聽到「不能」,就會覺得自己回到八歲了。(示意圖/非當事人照片/取自免費圖庫PhotoAC)
「妳瘋了嗎?這是喪志不是勵志吧。」我在莎拉上班的時候打給她,告訴她我的下一個勵志挑戰,她這樣說。
「試過的人都說他們的人生就此改變了。而且在經歷過《祕密》之後,我需要開始腳踏實地了。」
「這不是腳踏實地吧,根本就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莎拉說。
我四月的勵志任務非常極端,叫做「拒絕療法」。我稍微修改了這個療法的規則,因為這比較像是一個遊戲,而不是一本書。
遊戲目的很簡單:每天要至少被一個人拒絕一次。不是要「試著」被拒絕或「想辦法」被拒絕—是要真的被拒絕。幾年前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虐心的自我成長法時,覺得好扯,誰會想要對自己做這種事啊?
人生已經夠難了!但這個療法一直在我心裡揮之不去。在經過了一個月的假支票和幻想人生之後,我覺得自己需要拒絕療法。我需要現實世界的當頭棒喝。若是過去幾個月教會了我什麼,我想我學會了:越不想做的事,通常是我越需要做的事。
「但我看不出每天被拒絕要怎麼幫助妳成長。」莎拉說。
「這個遊戲背後的概念是,我們每個人都活在被拒絕的恐懼之中。我們有一堆想做卻不會去做的事,因為我們害怕別人說『不』。我們從這個遊戲當中可以學會,被拒絕固然可怕,但再可怕也死不了人。
玩過這個遊戲的人都說,其實被拒絕並沒有想像中容易,常常你以為對方會說『不』,結果對方卻說『好』。」
*本文摘錄自《勵志書實踐生存報告:我如何花一年的時間讀12本暢銷勵志書,並真的改變人生》
作者:瑪莉安・包爾
譯者:高霈芬
本文由 PCuSER電腦人文化 授權轉載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